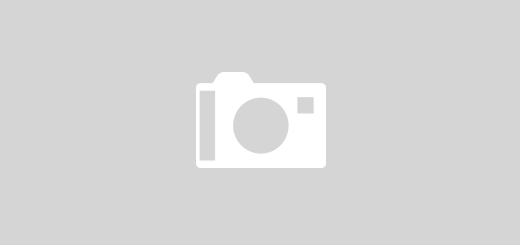阿里地带|青春小课堂:性、婚姻、教育及其他李银河访谈录……
12月1日是联合国第15个“世界艾滋病日”,记者对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作了专访。早在1999年,李银河就连续出版了《性的问题》、《虐恋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等一系列性学书籍,使读者对她的认识从简单的王小波的夫人扩展为一位意识超前思维严谨的知识女性。她所研究的领域在千百年来是为人们所回避与忌惮的,因此她本人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事实上,无论是观众面前的李银河,还是读者面前的李银河,都是儒雅而富有睿智的。她面对记者,就像面对一个朋友,谈艾滋、谈性、谈图书,当然也谈王小波。
性有点成问题
记:是什么契机使得你把视角转向同性恋人群的研究?
李:1982年到1988年我在美国留学,这期间作了回来研究的文献准备,当时准备的有婚外恋、婚前性行为规范、独身、自愿不育、离婚等,同性恋是其中的一项。回来以后在做独身研究的时候,遇到了我的第一例同性恋研究对象,通过他介绍朋友什么的(认识了更多的人)。因为线索非常宝贵,于是就慢慢做大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记:作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之一,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人群越来越被社会所关注。你如何看待“同性恋亚文化”?
李:亚文化一直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在同性恋研究里有一种说法叫异性恋霸权,同性恋处于无权的边缘的状态。那么现在国外由于同性恋亚文化有一种争取权益的斗争,他们要争取自己的空间,对主流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这一情况已经出现了,比如说在中国很多大城市出现了同性恋酒吧,网站上同性恋也特别活跃。
记:在中国的影视作品里,从最早王小波写的《东宫西宫》拍成电影,到后面的《霸王别姬》一直到现在的《蓝宇》,都是涉及同性恋的题材。是不是通过电影这种表现方式,同性恋文化越来越为普通大众所接受?
李:对。我认为同性恋在中国正在浮出水面。
记:1999年,你就出版了《性的问题》,同时还有《虐恋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等。尤其是《性的问题》,对当时的观念、制度、风俗习惯进行了质疑。现在你所质疑的这三方面有没有一些改变?
李:我想有好多东西已经在变了。比如婚前性行为是变得最厉害的。我在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作调查的时候,北京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是15%。最近我听到的最新资料在上海是69%,是通过计划生育办公室对婚前检查的妇女做得调查,广州是86%。这样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记:常言道“饱暖思淫欲”。现在我们社会的中心工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是不是性的问题更加突出了?
李:应当是这样。比如在50年代反右的时候,或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大家每个人都很怕犯错误,顾不了这么多。其实“性”就是关于人的快乐的问题,而快乐在当时很不重要。另外,比如说在困难时期,连温饱都解决不了,“性”肯定不能提上议事日程。“性”肯定是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善有关。
记:前一阵很知名的“夫妻看黄碟”事件,你怎么看?
李:现在夫妻在家里看黄碟的情况可能比10年前已经普通多了,也普遍的很。按现有法律,他(公安人员)不应该进去,因为现有法律是针对“传播和聚众观看”,它都不属于,它是夫妻两人私自看。有一个最有意思的批判“我们不仅看,我们还表演呢!”如果夫妻两个人“表演”,从性质上来说比“看”更严重,而夫妻在家里做的这个事情法律是绝对不会处置的,如果平时按这个道理来推的话,警察就绝对没有权力进他们家去。我觉得也到了改变法律的时候了,这法律已经很脱离实际了。
性的误区
记:婚姻是不是必须的?
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一个特别“中国”的观念。好像是必须的,谁都不能违背。国外记者问我,调查这么多同性恋,国内同性恋与国外同性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同性恋要与异性结婚,(因为)结婚的压力太大了。好多小城镇的同性恋者为这个特别痛苦,有自杀的,有逃婚的。在国外,像法国独居人口占25%,这样的比例可以看出婚姻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永恒的或是必须的。
记:性对婚姻有什么意义?
李:婚姻曾经是性的惟一的合法渠道。在(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不光是法律规定,人们的观念里也是,一个婚姻之外的人哪能有性啊?婚前性关系,不对;婚外性关系,更不对;要是一个单身的人与别人发生关系也不对。前一阵也在争论,非得把同居的人称为“非法同居”,我们觉得改成“非婚同居”比较合适。好多人的观念里觉得如果没有婚姻的形式要是有性的话,是非法的,是犯法的。自愿的免费的性是最高尚的,可实际上有好多是不免费的。
记:现在饭桌上的荤段子、手机里“荤面素心”的短信对性观念性教育有没有影响?
李:这可能也算是(性文化的)一种,但没有明显的边缘性。作为亚文化,应该有一个边缘的,共同的特征,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饭桌上的荤段子是一段时间流行起来的,真的谈不上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东北已经出了一套性教育教材,中国的吉林与瑞典合作的针对中国特色的性教材,有七八本,有给孩子的,有给父母的,有给教师的。通过几方面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而不是通过一两个黄色笑话。
性需要教育
记:你在美国生活多年,像美国这种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在影视作品方面已经实行了分级制度。在中国香港有些片子定名为“三级片”。那么在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这种制度。作为一位社会学家,你怎么看待电影分级制度?
李:我是赞成的。我觉得比一概禁止要现实得多。有些东西对青少年可能有害,像美国除有“R”级(限制级)之外,还有PG-13(parentgarden),就是要求13岁以下的孩子要家长领着(观看),体现了一种对人的关心。而且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不能拿一个13岁孩子的欣赏水平来要求全社会的人,比如说成年人看一点裸体应当是可以的,但也许13岁以下孩子看就有害,就划上级嘛,总比把全社会的欣赏水平都等同于中学生要强多了。
记:当前孩子的青春期性教育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在搞试点。你认为青春期性教育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李:其实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有过所谓“生理卫生课”,就是光讲构造,根本不涉及性,这东西没用的。真正的性教育,必须要讲性。你如果不讲性,他最后还是不知道这个行为跟生育有什么关系,还是要婚前怀孕,要传染性病。但是它可以分一下,给初中生讲什么,给高中生讲什么,给大学生讲什么。
记:具体说你强调哪一点?
李:现在新的性教育课本有的已经从小学开始,直截了当地来讲性。这样实际上破除了它的罪恶感,神秘感,给小孩灌输正确的性知识,其实是有利得多。虽然有一些家长希望孩子知道得越晚越好,我觉得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你与其让他懵懵懂懂地从一些不正确的渠道得到一些不正确的知识,还不如直截了当地给他一个平常心,对性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对性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有一些正确的知识。
王小波最爱写小说
记:今年是王小波先生去世五周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将网上模仿小波先生手笔的小说出了一个集子,叫《王小波门下走狗》,这里边有你感觉不错的或是说学得像的吗?
李:我已经看到了这本《王小波门下走狗》,还给他们写了序。他们这拨人,都是在网上写,有一天有人看写得不错,就把它编成了这本书。其中有一个人我觉得是比较棒的,武汉那边的一个高中生,姓胡,他写的是《岳飞传》、《杨家将》。
记:是叫胡坚(注:胡坚在书中用笔名文嚎)吧,我今年8月采访过他,挺有文采的。
李:对。他也是用那种时空跨越,在两边飞来飞去的写法,还是挺有才气的。很多青年看了王小波的小说,感受到了写作的乐趣,也特别想写作。当然其中水平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武汉的高中生是很有写作才能的。
记:对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人们评价不媚俗,有个性;而他的杂文不是投枪匕首,充满了黑色幽默。那么对于王小波的小说与杂文,你更偏好于哪一个?
李:反正他自己是特别偏重于小说的。如果有人夸他“你的杂文比小说”写得好,他就不太高兴。他觉得自己主要是一个小说家,以写小说为主。他的导师也是我的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老师,也写很多杂文。有一次他对我说,小波的杂文写得比小说好。
记:你最喜欢他的哪部作品?
李:我最喜欢他的《红拂夜奔》。
记: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叫《李银河推荐的十本书》,包括《日瓦格医生》、《老人与海》、《红字》等,不知是不是确有其事?
李:对,这是《南方周末》约的一篇稿子,约我写最喜欢的十本文学书,可不是学术书。
记:选这些书有一个什么标准?
李:我看了以前的读书笔记,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书。
>>>李银河著作:《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全文共3672字节
————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情感口述故事
本文标题:
文章链接:zone.alingn.com
文章来源:阿里地带
友情链接:✅女娲导航 ✅恋爱之书 ✅健康笔记 商务笔记 ✅健康杂志 ✅分享笔记 ✅健康社区